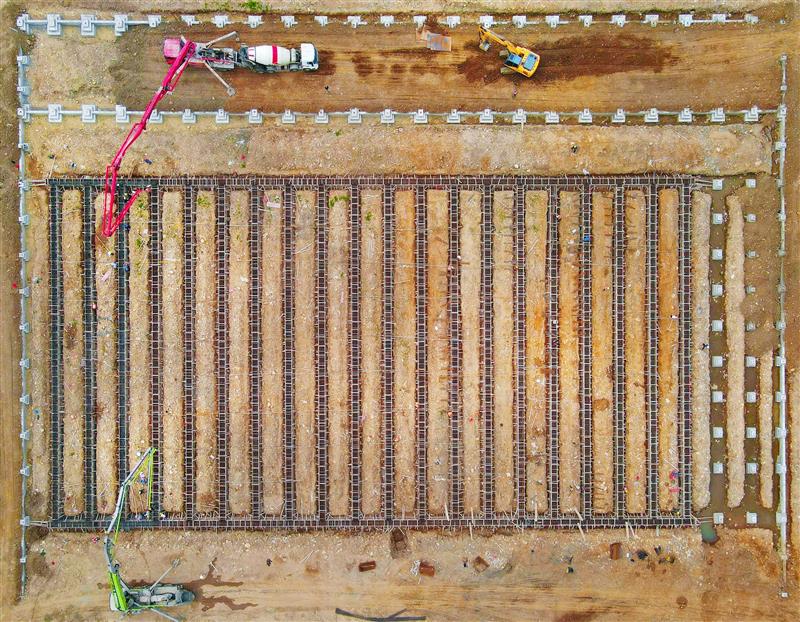汪烽/鸡汤泡炒米

鸡汤泡炒米(图片来自网络)
对于很多客居外地的安庆人来说,鸡汤泡炒米应该是最想念的味道。在一个陌生的城市,能吃上一碗地道的鸡汤泡炒米大概是对思乡之情最好的慰藉吧。
南京虽离安庆不远,所谓的徽菜馆也有不少,但我这么多年的观察,却少有鸡汤泡炒米,基本上都被臭鳜鱼、毛豆腐等味道厚重的菜品所霸市,以至于只要提到徽菜,不少人总认为徽菜除了口味重还是口味重。
安庆人对鸡汤泡炒米是情有独钟的,黄梅戏《打猪草》里就有一段关于鸡汤泡炒米的唱词,让这道安庆名吃融入了浓浓的乡土文化气息。著名琵琶演奏家方锦龙先生,是土生土长的安庆人,有一年在央视的一档节目里对鸡汤泡炒米备加推崇,道出了众多身在异乡、远离故土的安庆人对家乡味道的执着与想念。
鸡汤泡炒米好就好在鸡汤鲜美、鸡肉营养、炒米果腹,有饭、菜、汤三味合体之妙。试想,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回到家吃上一碗三者兼有的美食,那该有多惬意啊!但在那个贫瘠匮乏的年代,这却是一种奢求。我小时候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得到,而且只能是尝尝鲜,不管够,因为鸡汤和炒米得留着在正月里招待客人。
我的记忆里,在周边的十里八村,母亲这道菜做得最好。母亲说,这道菜的关键是选材,鸡要选至少两年以上的老母鸡,米要选当年产的长粒糯米。
鸡杀好以后,剁成四大块,趁着新鲜劲儿放入铁锅反复翻炒,焙干水分,然后迅速倒入热水,旺火烧开后除放适量盐调味外,不用搁其他任何调料,再灌入瓦罐中埋进灶堂,利用做饭留下的硬柴火的余热慢慢煨制,让土鸡天然的鲜美味得到充分释放。到第二天早上,一罐香气四溢的煨鸡足以把人从慵懒的梦乡中唤醒。
相较而言,炒米的制作稍显复杂。每到腊月农闲,母亲便开始制作炒米,为过年做准备。母亲炒炒米,我也就知道离过年不远了。
米要先用水淘去其中的沙粒、稗子等杂质,再用热水浸泡两小时以上,让米粒表面慢慢变得松软,捡一粒放在指尖一掐,不软不硬即泡好了。泡好的米捞出沥干后,放到室外再冻上一夜,表面的松软层经过一夜的冷冻,变得更加蓬松,炒出的米粒也更加酥脆。下锅前,在米中再撒几滴白酒拌匀,这是母亲的独门绝技。母亲说,这样炒出的米更加香醇可口。
炒制过程非常考验人的耐心和体力。为了让每一粒米受热均匀,口感一致,炒制时,每一锅只能炒一把米,一两多一点。满满一盆米,有时要炒上大半天。长时间的站立,加上灶火的炙烤,哪怕是在寒冬腊月,也能让母亲汗流浃背。为了不耽误白天干活,母亲总会选择晚上炒制。
开炒了,母亲便脱去棉衣,半依着灶台,用自制的由几根竹枝扎成的“小扫把”尖轻轻沾点菜籽油,在烧热的铁锅里来回一抹,便形成了一层薄薄的油膜,这叫润锅。待锅底泛起淡淡的油香,就抓一把米撒入锅中迅速搅动。米粒在高温的作用下发生膨胀,不一会儿便发出噼哩啪啦的声响,像是孩子们过年燃放的鞭炮。炒好的米粒,粒粒金黄,大小一致,抓一小把放进嘴里慢慢咀嚼,焦香酥脆,满口生香。在炒炒米的日子里,米香味、油香味和着灶堂里木柴燃烧的烟火味,弥漫着整个冬夜,香了小院,香了山野,也香了我和哥哥的馋猫嘴。
炒好的炒米自然冷却后,倒入一只不知道何时传下来的青花老瓷罐,罐口用两层草纸蒙住并用细绳扎紧,再盖上盖子封好储藏,静待过年时与鸡汤的完美邂逅。
前些年,老乡聚会,大家闲聊到为什么南京很多徽菜馆里没有鸡汤泡炒米时,有位老乡的分析颇有见地。他说,大概率是水土不服,没了市场。中国菜本身就没有绝对的标准,千人千味,类似于鸡汤泡炒米这种地域性很强的菜品,对选材用料、烹饪技法等都有特定的要求,这对菜品本身的口味会产生很大影响。同时,食客们对菜品原生地的生活习俗、文化环境等因素的知晓和理解,也会影响到对菜品的接受度。因此,离开特定的环境,同样的一道菜可能也很难吃出想要的家乡味。
其实,不管是什么菜系,都没有高下之分、优劣之别,只有合不适合、喜不喜欢、对口不对口。正所谓:嗜之者为美味,厌之者为毒药。但对于我来说,即使是山珍海味、美馔佳肴,也敌不过一碗浓郁鲜美的鸡汤泡炒米的畅快与满足。